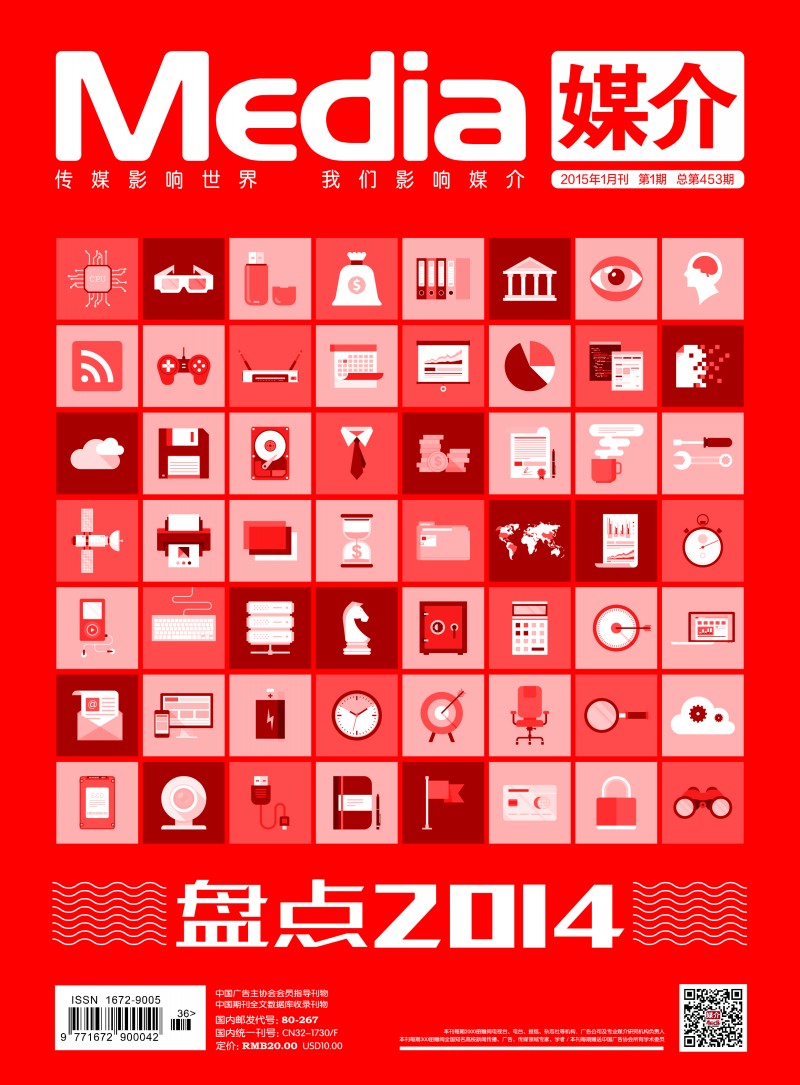
勇敢直面2015
每年1月编辑部都要照例对过去一年的传媒产业进行梳理与盘点,目的无非就是对过往进行总结,也对未来做出展望。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看待2014年的传媒产业?编辑部提供六大板块,既有高歌猛进烧钱不见钱的“新兴媒体”,也有寿命千年脱胎转型的“户外媒体”,更有夹板于新旧之间内外交错的“广电媒体”。笔者阅后有何感想?一个字:“迷”;两个字:“混杂”;三个字:“焦虑症”;四个字:“上下求索”。大的背景有两点,一是国家宏观经济降速已成“新常态”,二是打虎不断,大小虎多多,武松却是一人。我等观众从兴奋喝彩转入彷徨无着,“怎么办”也就脱口而出。
2014已经过去,2015就在眼前,媒体经营到底怎么办?这是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媒体无论新旧体制不分内外,既有的思维已经破绽百出,技术手段也陈腐老化,组织队伍呢,正是新旧交替军心涣散,显然,对于这个“怎么办”的回答并非易事。但是,也不得不答。笔者认为考察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较大的时间跨度,也需要捕捉其发挥关键作用的内在动因。1996年,笔者在研究媒体产业化的时候提出,中国的媒体产业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大市场、大资本与大媒体三个方面的交错作用。近40年来,虽然每个阶段媒体产业的经营发展的重点有所不同,但其内在动因并没有改变。
回望这四年的《媒介》杂志主打文章,其实与媒体产业的发展不谋而合。2011年,编辑部用“大国传媒”的概念去概括当时的传媒业,一连几期封面分别从大台、大网、大报、大剧、大营销等角度去描绘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的媒体之变。2012年杂志则用“新”做主题,涉及媒体的公共服务、新广电、新广告、新终端、新电视、新资本、大数据、内容银行等多个领域,体现的正是媒体产业所经历的由下自上的倒逼式的革命潮流。2013年杂志顺应前两年的思路,切入了媒体转型的问题,涵盖了节目创新、新兴受众、海外媒体集团变革、报业生死、OTT TV、户外媒体、电视能否为王、产业化等问题,并以媒介帝国主义收笔,阐述的其实是平台化、技术创新、资本浪潮等多种因素洗礼之下媒体机构的嬗变坐标。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编辑部进一步深入追问,通过关注大数据、电商、终端、精准、融合以及平台化,努力梳理新兴媒体的兴衰沉浮,几个关键的核心装置以及那个玄而又玄的经营思维。也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中央高层的声音:
2014年8月,习近平指出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笔者认为,《媒介》编辑部近年所展示的报道与观点,和中央高层的思路完全契合——以平台化的思路办媒体,以技术、制度和产业的方式解决融合的问题,以建立一批大型的可参与国际竞争的媒体集团为目标。
这,不正是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大思路吗?看不到虚无缥缈的“顶层设计”,也没有夸夸其谈的“理论创新”,实事求是一如既往。所以,无论2014年的传媒氛围如何诡异,经营道路如何崎岖,2015年媒体产业经营“怎么办”的抓手其实已经若隐若现:
第一,融合潮扑面而来,在融合潮流当中能否实现媒体的组织重构和规模,扩张至关重要。以前也常说“打造大媒体”,因为需要适应大市场环境。时至今日,媒体的经营规模扩张更为迫切。其实,中国的互联网媒体中BAT这样的寡头级企业已经成为产业竞争的标杆,块头越大越有分量。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靠传统业务起家的媒体机构也开始急起直追。在2014年,我们发现类似于湖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与SMG、华数传媒、浙报传媒等媒体机构分别在转型、融合的道路上探索确定自身的路径与模式,合纵连横群雄争霸成为媒体舞台的基本剧目。争霸范围广泛且角色串换频繁,令我们无从辨析。一方面,在业务、产品与技术上,这些媒体机构已经实现了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另一方面,在组织架构和经营运作上,不同的机构都采用了完全的公司化行为,所以,无法再用“体制内”或“体制外”作简单的区别;最后,在业务范围上,这些机构已经无所不包、不断拓展。所谓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界限几乎消弭殆尽。今后,对于争霸的媒体巨头的判断唯有三点,一是规模是否足够巨大,二是资本是否足够充足,三是技术是否足够强大,也唯有如此才能有足够的竞争力参与国际化的市场竞争。
第二,融合与扩张的关键在于资本运营,经营者是不是资本游戏的高手,决定未来的经营成败。从国际媒体机构的发展来看,资本无疑是最大的助力之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媒体机构的发展方向,我们也都知道,离开了资本,媒体的融合、转型、技术创新都难以实现。然而国内的媒体圈言及资本往往因体制问题而有所掣肘,一旦提及资本就让人联想到国外势力,就等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担心国有资产流失同时还惧怕影响了喉舌的管控。实际上,资本虽有国别,也有属性区分,但是,不论何种资本必然遵循利益最大化的游戏规则,择竞争优胜者而行,呈现无节操的工具性。2014年媒体产业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来的媒体运营高手随年事增大相继退居二线,取而代之的经营者必然是资本的游戏高手。资本来源不再拘泥于姓社姓资,也不在乎国营还是私募,只要能够为我所用,只要有利可图,只要能够冒险市场,统统取之用之,绝无羞羞答答扭扭咧咧。2015年的媒体产业经营,有无源源不断的资金资源,有无强劲的资本操盘手做军师后盾,市场胜败立马就明。媒体产业的竞争,真的到了这么一个阶段,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金钱万万不能。如此而已。
第三是市场空间看似很窄小其实无穷大,关键要看经营者如何去定义。市场空间不再是简单的狭小或者巨大,呈现前所未有的弹性,唯一的挑战在于媒体机构是否能够进入,进入的门票在于经营者的眼光与定义。对于中国的媒体机构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重新定义“市场”的概念,确认市场边界。这个市场不仅仅是广告市场,还应该是多元化的信息市场,可以通过业务拓展的方式进入的更加宽阔多元的领域,从而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这个市场不仅仅是媒体市场,也应该是整个文化市场,作为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机构完全有可能扮演多种角色进入多重的领域。这个市场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更应该是国际市场。伴随着产品国际化与人才国际化的发展,文化与传播的国际化发展势在必行,所以媒体的市场也应当是国际化的,从而成为能够与国外媒体巨鳄比肩的“文化传媒集团”。 文化市场的大小取决于文化消费的强弱,而文化消费的强弱取决于经济实力的兴衰。中国的大国经济已经成形,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大经济必然酝酿出大文化,这个大文化,既有物理空间的意味,也有规则制定的意涵。旧有的意识形态操控已经无法把握和引导这个大文化市场,必须要有新思维新方法,这是媒体经营者在国际文化市场克敌制胜的法宝。
勇敢直面2015。展望会有一线光明,但实践起来却又困难重重,正如数十年来中国媒体产业发展的迂回曲折起伏跌宕。我向来认为,真正驱动媒体产业向前的是业界经营者勇敢的实践与执着的探索,一种强烈的求生本能。每当学界与高层犹豫不决彷徨迷茫,业界始终没有停止摸索前行的步伐,在不断挫折的过程中寻找突破。
我称其为中国特色的“实践自信”。
2015年1月23日,第七届中国传媒趋势论坛,敬请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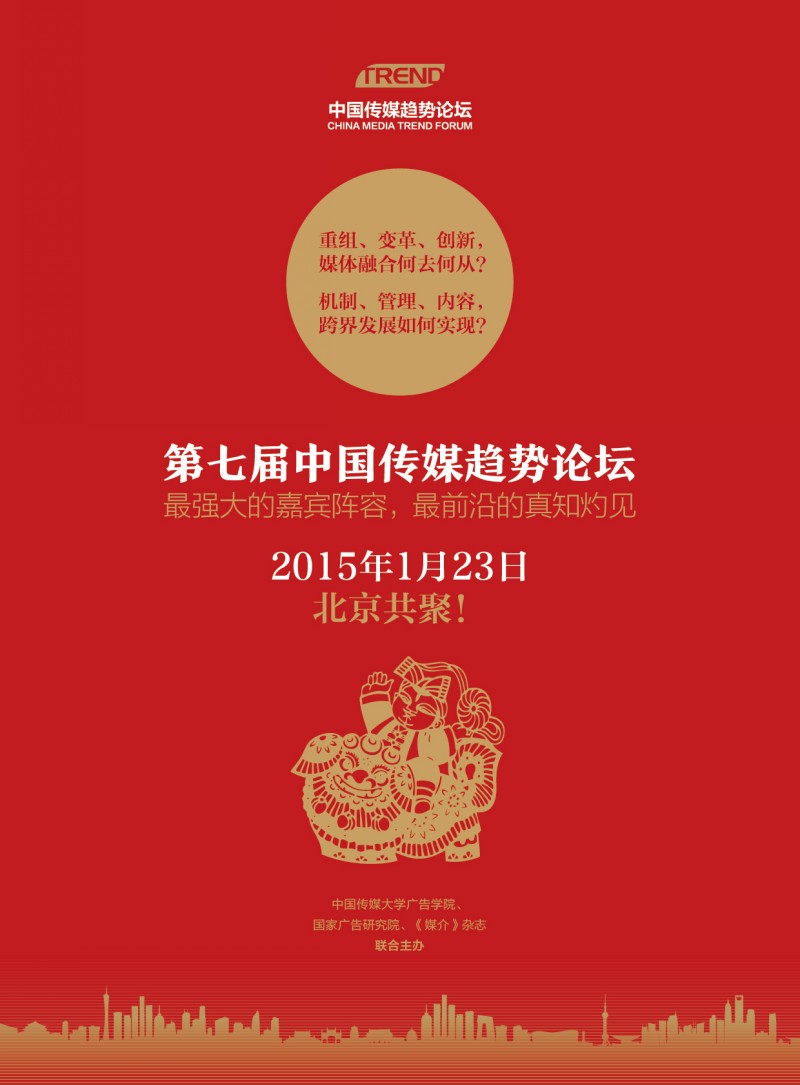
|


